“丑”的繁体字为“醜”,从“鬼”,“酉”声,本义不详,疑从鬼面引申为美丑之“丑”。“丑”是作为与“美”相对的概念而存在。关于“美”,从客观方面看,事物自然属性方面的和谐、比例、对称、多样统一等外观形式法则就是“美”。从主观方面看,人对自己的需求被满足时所产生的愉悦反应的反应,就是“美”。与之相似,“丑”大概也有两个不同指向的概念:从客观方面看,多用来形容人或事物的难看,即形式上的不和谐、不对称、不统一等属性;从主观方面看,人对自己的需求不被满足时所产生的厌恶或反感的反应,就是“丑”。在美学范畴中,“丑”指否定的审美形态,即“丑”本质上也是“美”,只不过是事物表面上的不和谐、不对称、不统一,由于实质上是“善”的、“真”的,而最终也是“美”的。一般评论范畴的“丑书”,往往还不是美学范畴中的“丑”,而是外观形式上的不和谐、不对称、不统一等属性,其中,有的是“以丑为美”,有的是真正的“丑”(伪艺术)。
正是这种概念的复杂性,关于“丑书”的讨论也变得十分复杂。艺术创变上的求新、求怪、求独特、求视觉冲击力等现象,并不必然成为“丑书”;至于“错字连篇”也不必然成为“丑书”;“江湖杂耍”往往是“俗书”,也不必然是“丑书”。“丑书”也不是近年来书坛才有的现象,自有汉字书写以来,“丑书”便存在。概有不由自主的“丑书”,有为“创作”故意而为的“丑书”。书法史上的穷乡儿女造像、敦煌经卷、题壁记事中的生拙书写,在当时属于想写好而写不好,由于其书写的纯真和历史感,在后世书家眼中却成了被取法追摹的对象,于是,清中叶开始的魏碑书法取代末流帖学书法成为必然。而“魏碑”并不必然对应“丑书”。至于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展厅书法的创变,故意以丑拙、不和谐为追求的现象,其中那些不“真”不“善”的,是故意而为的“丑书”。后者才是现在大家所批评的“丑书”。
20世纪80年代以来,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不断得以张扬,思想文化日趋活跃,艺术风格日益多元,艺术思潮不断涌现。在传统创作方式之外,还有三种创作潮流存在:一是通过丑拙书风张扬个性和彰显时代风尚,这是和典雅美观的书写风格迥然不同的创作取向,这一书法创作群体不断壮大,在1990年代全国“中青展”中成为冲出的“黑马”;二是以文字造型和绘画笔墨相结合的“现代书法”模式;三是受欧美文艺思潮影响的“书法主义”创作观念。它们异军突起,备受争议,与全国“三大展”偶尔相逢却又各成系统,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“非主流”的创变潮流。【参见李一、刘宗超著《新中国书法60年》,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。】在以上三种潮流中,第二种和第三种是怪异之风,第一种才是“丑书”创变现象。
现代的书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展厅来推动的。在作品中张扬个性,在展厅中取得夺人眼目的效果,是当代参展书家所极力追求的。于是,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被一些人所运用。同为“写字”式的创作,出现了与之相对的丑化字形的创作方式。这一类书家为追求空间构成的现代意味,不惜以破坏文人书法的典雅美与书写法度为代价。在不失汉字可识性的前提下,极力变化字形,打破常态汉字字形的谐调比例、匀称间架,营造了一种稚拙异常的风格,成为“字形的丑化处理”方式。他们往往取法民间书法、魏碑书法、写经书法的生涩趣味,把字形处理得丑拙怪异,以与传统文人的典雅书风拉开距离。他们最初虽然没有什么宣言和组织,但是相同的趣味却相互影响,以至于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群体。部分书家所倡导的“流行书风”和“艺术书法”模式,是其主要创变潮流。
近些年来,对“丑书”的声讨集中在公元2000年前后。当时,“中青展”(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)以倡导中青年的锐意创新为追求,试图与“全国展”拉开距离,出现了“混合体”式的流行风气。与对经典帖学主流书风的追寻相较(“新帖学”),人们对丑拙的流行风气的不满情绪愈加强烈。书法报刊不断出现对当时“丑书”的反思。有文章写道:“近年来,书法“以丑为美”几乎成为一种时尚,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倘若稍加留神,便可以发现一些面目雷同、奇丑无比的书法作品充斥各种报刊、展览之中,令人莫名其妙。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:一味地求生、求拙、尚奇、尚怪。有的假装童稚,有的故作老态。还有的干脆把汉字的点画结构作为机器的零件拆卸后重新组装,使之长画短写,短画加长,夸张变形,难以辨识。所谓的书法造型美、章法美、意境美,统统不复存在。给观众的则是满纸病态,突出了一个‘丑’字。”【惠立群《略谈书法“以丑为美”》,《书法导报》2001年2月21日,第1版。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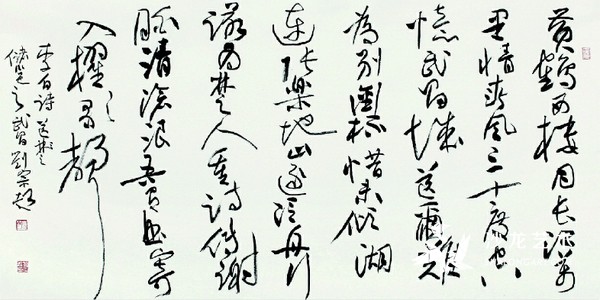
当时反对“丑书”最有影响力的言论,出自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刘炳森。他在答记者问时说:“大好形势下问题不是没有。甚至可以说,在某些方面还相当严重。”“有的年轻人根本不好好学习基本功,不好好学习我们中华书法的正统书风,胡涂乱抹,根本不像个样子,而大展却给这样的作品发了奖。”【刘炳森《书法的“主旋律”——答记者问》,《书法》2001年第4期第一版。】
这些对“丑书”创作现象的批评和反对,加快了书风向帖学经典转变的速度。在2002年首届“中国书法兰亭奖”作品展评选后的答记者问上,评委会主任刘炳森说出了这一变化:“过去历次大展都产生过导向作用。但我觉得过去有些展览的导向导出了问题,比如导向‘制作’,导向‘歪七扭八’,导向‘丑’,大大削减了书法内在的本质意义和文化品格。这次初评时,仍然有一批上面说到的这类作品,我感到很伤心。不过经过第一轮初评后,特别是复评后,忽然感觉到安静了许多,那些伸胳膊蹬腿,乌烟瘴气的东西一下子没有了。一种祥和、文雅的气氛扑面而来。我们不是一直认为‘中和’之美是书法的高境界吗?这种气氛就应该是中和之美的显现,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特征。”【《评委会主任刘炳森答记者问》,《书法导报》2002年5月29日,第1版。】
2002年以来,随着书法的纵深发展,回归传统的程度不断深化,书法界对“经典”和“大家”的呼声渐高。回归帖学经典,取法“二王”书风成为主流取向,展厅书法发展出现了深入书法传统、重温书法经典的新气象。而近年来的“丑书”现象,创作的队伍仍是来自于前些年的“流行书风”和“艺术书法”阵营,从观念上、规模上、强度上并未超过以前。一些“江湖杂耍”,在国内外招摇过市,或“书中有画”,或“打把式卖艺”,粗俗不堪,浅陋怪异,实非本文所讨论的“丑书”。
简言之,本文所讨论的“丑书”,或与“美”的形式、理念相悖,属于真正的“丑”;或不乏创变的探索,丑拙中见追求,“丑”中见“美”,成为美学意义上的“丑”。美学意义上的“丑”并非真正的丑陋,而是通过“丑”的外在形式———不和谐、冲突、夸张、怪诞,表达了感情之“真”或道德之“善”,才使“丑书”成为艺术创作的一种特殊形式。这类似于中国戏曲表演主要行当之一的“丑”。丑虽居生、旦、净、末之后,但由于他们在外表丑陋的表象下,或机智幽默,或冷讽热嘲,或突破,或反抗,符合事物之“真”或道德之“善”,才在表演中见功力、见人物、见本真,赢得了“无丑不成戏”的美誉。“丑书”,或否定,或反叛,或夸张,或怪诞,好坏本不能一概而论,但是,如果离开“真”和“善”,便成了真正的丑陋!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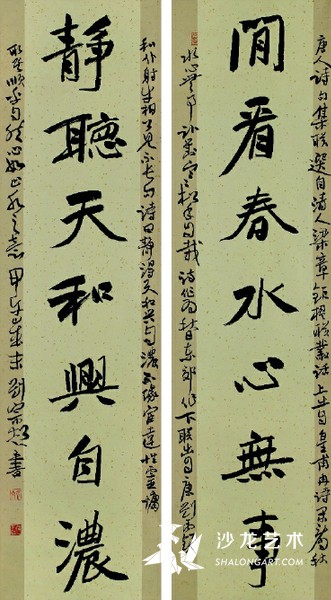


 陕公网安备 61011302001229号
陕公网安备 61011302001229号
